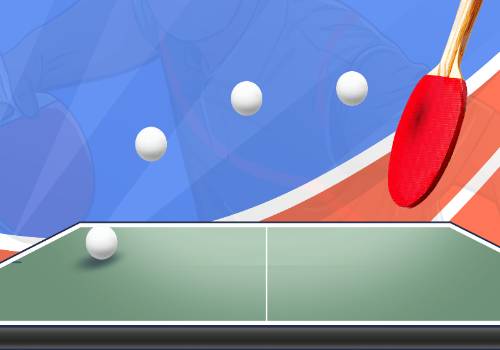父亲的《数蛋歌》
作者:王干
爷爷开过蛋行、米行、草行,到父亲这一辈公私合营了,伯父去粮站当了站长,父亲去供销社收蛋,叔父考上师范,当了小学校长。爷爷自己也去供销系统当营业员,先在镇里,然后去了村里。小姑姑从小就被宠,闲着在家。
里下河的禽蛋产量很高,源于家禽饲养的量很大,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家禽研究所就设在里下河的邵伯镇。里下河的蛋品远销上海、南京、杭州,甚至海外。父亲将各村商店送上来的鸡蛋、鸭蛋、鹅蛋集中起来,再送到泰州食品公司,有点像中转站,先收购,再卖出去。这里面有没有利润,不知道,好像那个时候也不讲究利润,没有听父亲说过盈利还是亏损的事情,也没有见他为利润的高低焦虑过,肯定没有考核指标。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父亲也收农民零散的鸡蛋,陈堡镇附近的农民喜欢到父亲的店卖蛋,他们说,老王的秤准。
“老王的秤准”,平添了很多事。没钱买盐买油了,两三个鸡蛋,甚至是一个鸡蛋,农民也拿过来卖。其他商店的店主背地里议论说,老王的神经搭错了。有时候父亲出差了,农民们就等他回来。因此,父亲的“生意”总比别的店好。
父亲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收购各村商店送过来的大批量的鸡蛋,鸭蛋也有些,鹅蛋很少。这些村店的营业员划着船,运着一箱又一箱的蛋来到镇上的供销社,卖到父亲的店里。当时装蛋的箱子并不统一,各家有各家的包装,到供销社要腾转过来,卖家和买家就用手把鸡蛋一个一个地从这个蛋箱转移到那个蛋箱。
这是枯燥的活,也是技术活。在一般人看来,一船的蛋怎么也得半天才能倒腾完,但父亲他们很熟练,一只手可以抓六个蛋,两只手抓十二个,一会儿就完事儿了,父亲一个上午可以卸三船的蛋。不会数蛋的人很容易把鸡蛋弄破,但鸡蛋在父亲他们手里像玻璃球一样,玩得滴溜溜地转。
那时候没有磅秤,他们就数鸡蛋的个数,我小时候总听父亲唱《数蛋歌》。《数蛋歌》是我命名的,有点类似劳动号子。他们一边数蛋,一边唱,歌词极其简单:“一手啊,二手啊,三手啊,四手啊……”一箱唱完,得出“手”数,就能估算出大约多少斤。后来有了磅秤,父亲说,数蛋和磅秤得出的斤两几乎没有出入。
父亲的收购站里还有一种纸糊的用来照蛋的设备,我称之为“照蛋器”。时间长了,蛋会变质,父亲他们的术语叫“流黄”或“散黄”。好的鸡蛋的蛋黄是圆圆的,边缘是齐整的。最坏的是蛋黄发黑,那是真正的大坏蛋。散黄的鸡蛋一般也可以吃,就是不能送到食品公司了,因为食品公司的蛋有的要出口,所以父亲他们很认真地检查,不能让中国的坏蛋流传到国外去。
父亲其实很少去照蛋,更多的时候凭手感判断蛋的好坏,如果感觉鸡蛋轻了,就去照一照,看看有没有散黄。所以,收购站的那个照蛋器,我用得最多。六七岁的时候,我常常到父亲的收购站里,把鸡蛋对着照蛋器上那个圆圆的孔,光透过白纸照进鸡蛋,蛋黄和蛋清是清晰地分开的,蛋清透明无瑕,乳汁一样弥散着,而蛋黄圆圆的,像一轮金黄色的小太阳。
时间长了,我还能分清色蛋(即受精鸡蛋)与普通鸡蛋的区别,色蛋的表壳有一两个白点。色蛋能孵出鸡雏,普通鸡蛋则不能。每年春天,有炕坊来订购色蛋回去孵化小鸡,因此色蛋的价格要高于普通鸡蛋,父亲就有意地将色蛋用单独的蛋箱存放。
过了春天,色蛋和其他的蛋就放在一个箱子里了,因为炕坊一到夏天就关门了。也并不是所有的色蛋都能孵化出小生命来,那些蛋叫“哑蛋”。很多哑蛋已经生长出鸡鸭的雏形,让人顿生悲悯。家乡的炕坊总是将这些哑蛋埋到土里,做肥料。而南京人则爱吃这种哑蛋,他们称之为“喜蛋”,用水一煮,然后蘸点盐,吃得津津有味,美其名曰“活珠子”或“旺鸡蛋”。里下河的人对此是非常鄙夷的,说“他们饿疯了”。
小时候最难忘的还是父亲数蛋时唱的《数蛋歌》,尤其是他和那个叫金涛的伯伯一起数蛋的时候,两人配合默契,歌声也极其有韵味。金涛从蒋庄自己一个人划船过来,每次带来的蛋数量很大,因为蒋庄是个大庄子,人口多,养家禽的也很多。后来奶奶告诉我,金涛原来是我们家蛋行的大伙计,人很好,会做生意,父亲小时候最喜欢和他玩,尤其喜欢跟他学数蛋,家人不让父亲数蛋,也劝不住。现在两人有机会一起数蛋,那叫一个不亦乐乎,仿佛是上了《星光大道》的歌手。他们的歌唱中,有少年的记忆,也有兄弟般的情义。
我是能理解父亲这一乐趣的,我那时候手小,自然抓不住六个鸡蛋,于是和弟弟用玻璃球和小石子当鸡蛋数,一边数,一边唱:“一手啊,二手啊,三手啊,四手啊……”循环往复,乐此不疲。心想,等我长大了就好了,一手也能抓六个鸡蛋。后来弟弟患脑炎去世,我数蛋没有了伙伴,再也没唱过。
每个村里来的营业员都会陪同父亲数蛋,但有一个人例外——我爷爷。
爷爷排行老五,人称“王五”。做过蛋行、米行、草行老板的他,后来当起普通营业员,好像不太适应。他的工作从镇上到乡里,再到村里,最初还是大庄子,后来到了全镇最小的陈林村。我曾以他为原型创作小说《除夕·初一》,写里下河深处最小的一个村庄营业员的日常生活,在爷爷去世十年后发表在1986年第11期的《安徽文学》。
爷爷到父亲这里卖蛋也是划船来的,但他不会划船,也不学,他雇村里的一个小伙子当船工,自己坐在船头看小伙子划船,不时给小伙子递烟。村里的人都愿意为王经理(村里商店就他一人)划船,说“王经理大方”。
爷爷来到父亲的蛋品收购站,从不数蛋,只是看着父亲数。父亲自己一个人数,但不唱《数蛋歌》了,爷儿俩一言不发。卸完蛋,对一对蛋的数量,然后开票。父亲留下存根那一页,爷爷拿着支付的那一页,与他人无异。爷爷有时候看到我,咧着嘴,朝我笑,露出被烟熏得黑黄的牙齿,我感到有些害怕,赶紧躲开,他讪讪地有些尴尬。父亲在我后脑勺上拍一下,叱责我不懂事,爷爷赶紧叱父亲一句:“孩儿小,别吓着。”我哇哇哭起来,一路奔回家向妈妈诉苦“爸爸打我”。
后来,金涛伯伯被提拔了,调到供销社当领导,因为他出身好,人缘好,工作又有成绩。有一次,他看到爷爷来卖蛋,就主动和父亲把爷爷那船蛋数完,老哥俩数着数着又唱起来了:“一手啊,二手啊,三手啊,四手啊……”
爷爷站在一边,抽着烟,只是看着,一声不吭。
金涛数完蛋,向爷爷微微鞠了一个躬,离去。
1976年,爷爷去世。2015年,父亲去世。金涛什么时候去世的,我不知道,我问母亲,母亲说:“早不在了,他儿子都去世好几年了。”
世上再无《数蛋歌》,一手二手三四手……
《光明日报》( 2023年04月07日 15版)
X 关闭
- 父亲的《数蛋歌》
-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会见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; 要闻
- 康乐卫士:4月4日接受机构调研,首创证券、开源证券等多家机构参与 今日聚焦
- 视讯!特朗普批拜登:人民币可能取代美元 将是美史上最大失败
- 和谐汽车(03836)4月6日斥资约18.62万港元回购18.96万股_快播
- 包茂高速岑溪大隆段发生新能源车事故,死者系“85后”法官
- 热消息:数字化春耕春管为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
- 花溪科技北交所首日盘中破发平收 去年营收净利双降
- 清理违规搭建,修理破损墙面,打造特色街区 泉州市区状元街启动立面提升整治
- 《英雄联盟》黎明使者雷克顿皮肤价格一览
- 【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】23厦国贸控SCP004票面利率为2.7300% 今日关注
- 云南蛮夷之地是指哪里_蛮夷之地是指哪里
- 借代和比喻的区别_借代 环球关注
- 智通港股通占比异动统计|4月6日
- 焦点速递!构建“六位一体”心理健康育人新格局
- 武汉凡谷:4月4日融资买入3533.53万元,融资融券余额1.29亿元|环球快讯
- ChatGPT停售Plus服务_资讯
- 佳木斯中院“三争晋先”推动工作落实|每日关注
- 成功购车送小礼品
- 印花税口诀
- 宇智波佐助
- 待怎么组词语 待可以组什么词语_天天最新
- 全球热门:一吨水等于多少升水_一吨等于多少升
- 每日热闻!超市中哪些白酒值得喝?这4款遇见别错过,老一辈常喝的口粮酒
- 天天快资讯丨“菜篮子”“果盘子”里看种业振兴——来自2023中国种子大会的一线观察
- 怎么做折线图显示月份不全呢(怎么做折线图) 环球微动态
- 淘宝网怎么进不去(淘宝进不去怎么办)_每日热门
- 花儿与少年第三季
- ios16.5更新了什么 苹果ios16.5更新内容/续航/发热/信号一览[多图]_环球微资讯
- 中医治疗眩晕一则,平肝潜阳,化痰降逆 世界热头条
- 涉案80万!蔡振华疑似被查,妻子一张图进行辟谣,刘国梁紧急回应
- 全球即时:七夕节普通朋友可以送礼物吗
- 每日看点!抢抓农时忙插秧
- 平均缴费指数高好还是低好_平均缴费指数Q是怎样计算的
- 世界观点:Tale_企鹅的故事英语观后感600字 极品飞车观后感600
- 人民日报发声后!中央政法委将严查!刘国梁危险
- 天天百事通!省、市联动 四川启动2023年“西部计划”招募工作
- 网上买的酒精怎么鉴别是不是75%? 头条焦点
- 中煤能源(01898):“18中煤02”票面利率将下调250个基点
- 降价车也不好卖了?特斯拉一夜暴跌2700亿
- 喜提大众速腾 车牌选号全是“SB”结尾 女车主:它是不是骂我呢? 世界热头条
- 文学新著再现抗倭民族英雄柯乔的骄人业迹-全球速讯
- 全球球精选!销量腰斩、经销商退网,留给这7家合资车企的时间不多了?
- 环球速读:NCAA总决赛-康大灭黑马夺队史第5冠!热门秀名场面
- 民航局:进一步强化协同配合,为国产民机运营提供良好环境
- “森林里的中关村,公园里的科学城”!北京海淀:生态代码写入创新程序-当前要闻
- 抓好食品安全 全力织好校园卫生“安全网” 世界今头条
- 天天快讯:越秀资本:4月3日融资买入2796.51万元,融资融券余额5.17亿元
- 东野圭吾著作在日累计销量破亿
- 国脉文化:4月3日融资买入1960.58万元,融资融券余额2.69亿元
- 热推荐:部分商品售罄!“回南天”持续,抽湿、烘干设备成广西“抢手货”
- 腰粗大树刮断砸中小轿车 女车主:不慌 先拍个视频
- 4月3日基金净值:泰达宏利景气智选18个月持有混合A最新净值1.0918,涨3.05%|环球时讯
- 河北发布大风蓝色预警,局地可达9级
- 焦点播报:考摩托车驾照要多少钱_学摩托车驾照多少钱
- 要闻:AI生成的合成图像泛滥且真假难辨 政策监管势在必行
- 航发科技(600391.SH)2022年度净利润4660.67万元、同比增长118.96%
- 最好的礼物百度云
- 人民币国际化,再迎大动作!
- 今日关注:sqlserver2022产品密钥_求SQL Server 2012的产品密钥
- 真我GT Neo5 SE正式发布,1999元起售_最新资讯
- 4月1日起杭州少儿公园恢复正常门票收费|天天观点
- 泰国首富中国养猪
- 天然气壁挂炉怎么设置温度_天然气壁挂炉怎么上水
- 水八仙是指哪八仙_水八仙是指哪八仙苏州
- 今日讯!赵诣管理“泉果旭源”宣布将放开申购,短期将关注这两类机会
- 第三方物流的特点不包括哪些_第三方物流的特点
- 旺子岛现在属哪县_旺子岛
- 【全球独家】体恤是什么意思啊_体恤是什么意思
- 上帝的愚拙与聪明的人_视焦点讯
- 全球资讯:挑山工教学设计_挑山工
- 全球观速讯丨九年级数学中考备考计划表详细_九年级数学中考备考计划
- 特斯拉直销VS比亚迪经销:销量放缓下,谁劣势更大? 即时看
- 快报:Vignale的惊人法拉利375America可以在拍卖会上获得数百万
- 恒华科技(300365.SZ)现跌5.22%报7.99元 最新市值47.9亿元
- 5年期以上LPR利率下调15个基点 对楼市影响几何?
- 复工预期带动一周反弹逾10% 新能源车产业链迎来新机遇!
- 大批零售商财报密集来袭 美股能否迎来新转折点?
- 欧洲构建本土电池产业链曙光初现!电池回收技术开始商业化落地
- 发挥 LPR 改革效能!央行公布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
- 销量暴跌厂商砍单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换手机?
- 黑龙江七星河湿地:近万只候鸟回归报春
- 吉林市:加快隔离房源腾退 提高周转使用率
- 吉林市对重点街区、人员开展“抗原自测+核酸单人单管”入户采样
- 【挑战365天正能量速写画】第122期:爸爸牺牲5年后女儿继承警号
- 退役军人成最“淡定”外卖骑手
- 浙江嘉兴南湖区划定封控区、管控区、防范区范围
- “以稀为贵”的羊肚菌,在武汉也能种好
- 严防外来物种入侵 北京海关守护国门生物安全“第一道防线”
- 抗疫MV:习惯你在身边
- 新疆昌吉:丹霞映雪山戴冠
- 武汉观测记录野生鸟类增至357种 数量创新高
- 多只蒙新河狸被拍深夜“同框觅食”
- 子非鱼焉知鱼能不能做加减法?国际最新研究发现算术好的两种鱼
- 陕西宝鸡今日解除3个封控区1个管控区
- 司法护航 “世界贯木拱廊桥之乡”廊桥文化遗产焕发新活力
- 为农献智的“85后”:让乡村振兴搭上“智慧快车”
- 2021年大气环境气象公报:全国大气环境继续改善
- 今年是否出现了倒春寒?国家气象中心回应
- 战“疫”有声 福建宁德高校学子文体生活“热度”不减
Copyright © 2015-2022 华声商报网版权所有 备案号:京ICP备2021034106号-36 联系邮箱:55 16 53 8 @qq.com